我们天上见

母亲卑微如青苔
庄严如晨曦
柔如江南的水声
坚如千年的寒玉
举目时
她是皓皓明月
垂首时
她是莽莽大地
——洛夫《母亲》
又是一年七夕,又是母亲的生日。
清明回老家扫墓,与往常一样,摆好父亲准备的点心和水果,插上姐姐买的鲜花,我依旧在母亲坟前哭了很久。哭的原因,可能是懊恼于我的平庸,可能是心有不甘,也可能就是单纯的想她。
过了这么久,两年前的一切还是历历在目,恍如昨日。母亲的离去是我人生中最重大的转折,母亲走了,我的家不再完整,心空了一大块。我用了两年时间去填补心里的这个洞,可惜没成功,洞还在那里。只不过,我已经能够正视这块儿坍塌,并尽可能做到与它和平共处,甚至刻意地忽视它的存在,以保证我还能正常的生活着。
我是个性格内向的人,既不善于表达,也不善于找人倾诉。加上自诩为知识分子,于是每到重要节日,我就有想写一篇悼文以纪念她的冲动。这篇文章,半个月前就开始酝酿,但严重的拖延症一直苦恼着我,以至于今天才兑现。
我要写的事情,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,因为母亲一生足够卑微、孱弱、平庸;也不是什么矫饰矫情的催泪文,尽管确实有很多事情足够引起我难过的回忆。但我还是希望我的亲人、朋友能够读完它,或含着泪,或含着笑。这不是为了忘却地纪念,而是想趁着我还记得,我要把母亲写下来,倘若侥幸活到满头白发的年纪,还有这么一些美好的记忆可以陪伴我走过后面的人生。

父母爱情
母亲二十岁嫁入徐家,正值梦幻年纪。翻看老照片,长发结辫,虽是黑白图像,但仍可看得出母亲明眸皓齿,脸庞温润如瓷。
“你爸当年可是个好后生,说媒的很多”,母亲笑着,羞色半收半隐如三月桃花。这是母亲少有的骄傲时刻。
第一个孩子出生后,初为人父人母的喜悦占据着家里的主导地位,母亲也觉得生活厚待于她,满月酒、庆周,一个不落。随着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孩子的出生,拮据逐渐蚕食着生活,母亲便深感岁月蹉跎,亦能隐隐揣摩到她当年的些许失落。
“那时真是太难了,每天一睁眼,就想着怎么给你们做吃的”,母亲语气惆怅,但表情略带自豪。是啊,抚养四个孩子,照顾忙于工作的父亲,在那样艰难的日子让一家人吃饱吃好,本就是功德一件。
母亲爱干净,做的一手好菜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巧妇虽难为无米之炊,但这难不倒母亲,她总是绞尽脑汁变换着花样,争取让平淡无奇的食材可口一些,更可口一些。春天榆钱儿做饭,夏天豆角焖面,秋天腌制蔬菜瓜果,冬天各种干货,母亲总能做出与众不同的味道和样式,惹得邻居羡慕。
我最爱吃母亲做的手擀面,和面、擀面、切面,母亲就像魔术师一样,瞬间将一堆面粉变成一根根筋道的面条,一气呵成。此时的父亲在灶膛添柴,看着母亲一手拿油瓶,一手操锅铲,站在香气中,如同锅里的饭一样可亲。
他们就是这样,用青春和爱为佐料,扛着贫瘠的生活,烹制一道道晚宴,滋味厚重,淋漓铿锵,养育着我们姐弟四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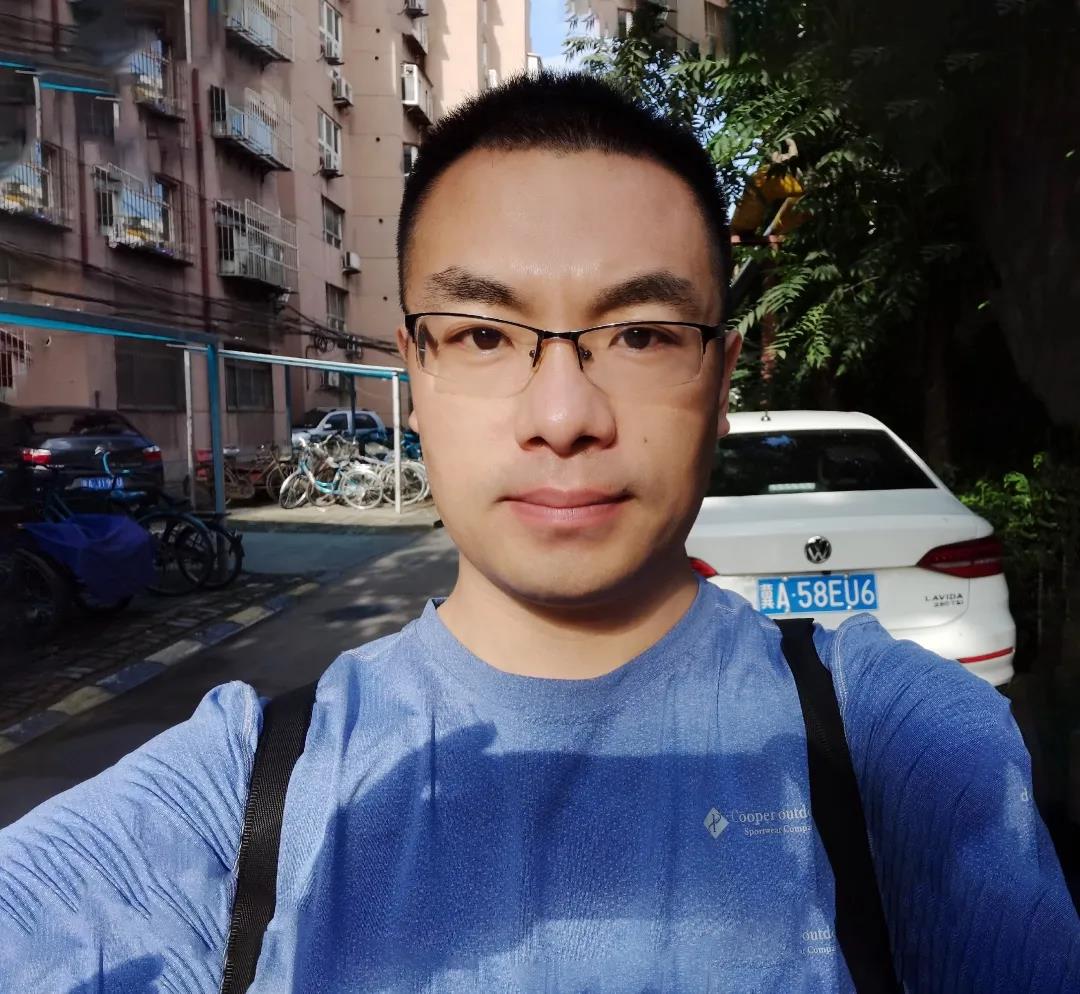
小狗
一天晚上,母亲串门回来,怀里抱只小狗。
这是一只农村最常见的土狗,巴掌大小,浑身黄毛,骨瘦如柴,眼睛暗淡无光,时不时舔一下母亲的手。母亲说,从邻居家出来,这只小狗就一直跟着她,打骂不走。天儿这么冷,在外面肯定冻死,就把它抱回来了,明天再放回原处。
我央求母亲把小狗养起来。母亲面露难色,家里的光景并不富裕,再小的狗也要吃饭。还是父亲说:“孩子喜欢,就养着吧。”
母亲找来一块干净的布,沾上热水,将小狗简单地擦干净。又找来一只碗,剩饭泡点儿菜汤,当做它的晚餐。小狗显然是饿坏了,吃得狼吞虎咽。母亲笑着说它是饿死鬼超生。
我给它起名叫小黄。
小黄很小,小到一只碗就能够盛下它,小到仿佛再送到屋外马上就能被冻死。喂完饭,母亲从外面找来一个装药的纸箱,又从柜子里翻出一些不穿的旧衣服和棉花垫在箱子里,放在炕头的窗台上,当做小黄的家。小黄很乖巧,吃饱喝足后,趴在小窝里,时而煽动几下耳朵,时而长舒一口气,睡得香甜。母亲说:“小黄以后就是你的了,你要好好看管。”
小黄在母亲的喂养下很快就长成了大黄,每天都守在我放学的路上。小黄可以轻而易举地扑在我肩头,舔我的头发和脸,或在我身前身后连蹿带跳,不时汪汪几声;或者顺从的趴伏在地,让我抚摸它的头,尾巴扫得尘土飞扬。每每于此,母亲便假装吓斥几声,告诉我小黄太脏。
吃饭的时候最逗,我们一家团坐在炕上,锅碗瓢盆叮叮当当。小黄不敢上来,只能蹲着地下,眼巴巴地看着我们,馋得急了,就原地跳几下,发出哼哼唧唧的叫声。母亲总是会从自己的碗里夹出一点儿饭或菜来安抚它焦躁的胃肠。
小黄伴我童年,小黄死于年长。
母亲去世后,大姐的生活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。有一天,我问她:“你怎么不养只小狗或小猫来陪你?” 大姐说:“我不喜欢猫狗,咱妈也不喜欢。”
我的眼泪流了下来。

偷钱
化疗后母亲时常口苦,我买来水果糖,剥好后放她嘴里一颗。母亲说,你还和小时候一样。
我的童年很快乐,快乐的源泉,可能就是零花钱。父亲每天给我五毛,在那个水果糖一分钱一块的年代,五毛钱着实是一笔巨款,足够我逍遥一天。每次买来水果糖,我总会先剥一颗给母亲,母亲则是下意识地拒绝,并说我不爱吃,周而复始。但她拗不过我。然后,是我的父亲,我的姐姐、哥哥。
有一天,我在家里翻箱倒柜,突然从柜子的夹层里发现一个纸包。打开一看,是好多钱。确实是好多钱,年少的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。我想放回原处,但傻瓜瓜子、跳跳糖、三鲜伊面以及奶油雪糕的诱惑让我无所顾忌。我偷了五块钱,一周花完,小朋友们投来羡慕的目光,我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见母亲没察觉,陆续有了第二次、第三次。
母亲一生务农,斗字不识一升。她没有挣大钱的能力,靠着织毛衣或绣花贴补家用,每月收入不足百元。
我继续向小朋友炫耀着我的优越,母亲出现了。她把我拉到操场边,满脸的怒气揭示着我东窗事发。母亲站在那里不说一句话,我站在夕阳下瑟瑟发抖,抽泣不停。良久,母亲擦干我的眼泪,说:“我是担心你变坏了。”
不远处的人家正在准备晚餐,炊烟飘动,仿佛房屋在轻柔呼吸。一朵云染着金边,在山峦上轻轻荡漾。
母亲说:“天要黑了,回家吧,妈不告诉你爸。”
母亲走在前面,我跟在后头。夕阳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,我踩着她的影子,亦步亦趋,不敢靠近。在八岁的那个傍晚,我知道了母亲的不易。
母亲的眼泪
姥姥去世了,那年我刚上大一,准备期末考试。因为怕影响我的学习,家人一致决定瞒着我。等我放了寒假回家,姥姥已经下葬。我和姥姥不熟,从小到大,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会超过一个月。所以姥姥去世后,我哭了,但心里并没有那么伤心。
腊月十五晚上,母亲说:“儿子,陪我去街上吧,给你姥姥烧点纸”。那天可真冷,路灯忽明忽暗,风吹得电线呜呜响,像极了恐怖电影里的鬼叫声,听得我头皮发麻。母亲跪在冰凉刺骨的地上,反复说着想姥姥的话,悲恸不已。但那时的我,只觉得冷,似乎不屑于母亲的泪水与悲伤,甚至有些烦躁,烦躁母亲为什么要哭那么久。
我甚至怀疑我是个石头心。
直到三个月后,我在街上见到一件花衬衫,我的第一反应是给姥姥买一件,顿了几秒后,我感到呼吸困难,心开始剧痛,我才意识到,姥姥真的走了,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。
蒋雯丽先生的电影《我们天上见》里有这样一段对话很有意思:
小兰问姥爷:“姥爷,你可怕死呀?”
姥爷说:“不怕。”
小兰:“为什么?”
姥爷:“活着跟你在一起,死了跟你舅舅他们在一起,两边都是我的亲人。”
如今的我,遇到了和当年母亲一样的境地:一样的悲苦,一样的撕心裂肺。但我坚信我比母亲幸运,因为姥爷还说过:“人死了以后,坏人在地下,好人在天上。”
是啊,我们天上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