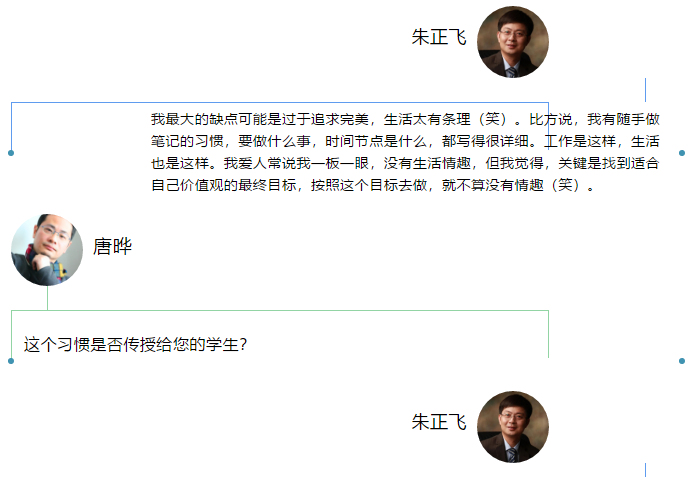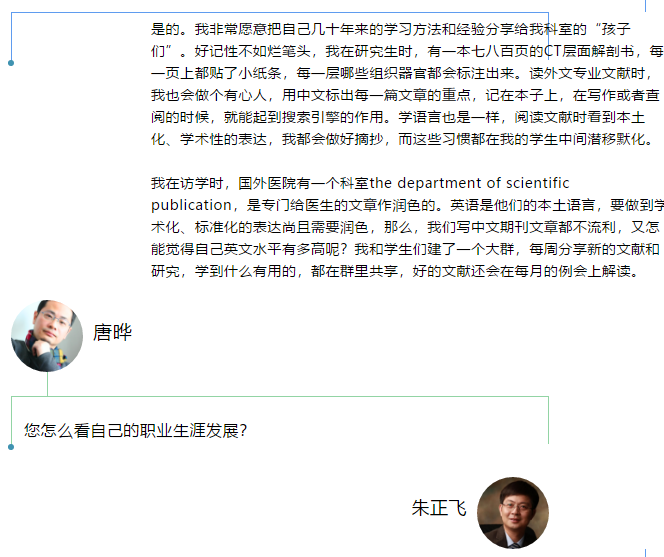朱正飞 也许,人类正需要向肿瘤细胞学习
人 物 介 绍

朱正飞,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射治疗科主任医师,肿瘤学博士,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临床研究中心主任。擅长常见胸部肿瘤,包括肺癌、食管癌、以及纵膈肿瘤的放射治疗及综合治疗。任中国医药教育学会肿瘤放疗专委会副主任委员、中国临床肿瘤学会(CSCO)青年委员会常务委员,在以第一/通讯作者身份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学术论文50余篇,其中SCI收录的学术论文30余篇。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、上海市“医苑新星”杰出青年医学人才计划。

采访笔记
采访医生有些年头了,我也常常听精于此道的“业界领袖”在私下里这么说:癌症源于基因的突变,而这种突变基因导致的癌细胞,有时会展现出永不停止的分裂,它们可以一直分裂下去,没有衰老的痕迹,这透露出永生的意味——这种带着永生意味的分裂,却会摧毁我们的身体,带来无可避免的死亡。
这真是一个绝佳的隐喻:永生带来的即是死亡。这使我隐约觉得,癌症是人类通向永生的最后一道大门,但这道大门背后,并不一定是世外桃源,有的可能只是万丈悬崖。
我们的聊天洋洋洒洒,他的语言里闪烁着微光,自始至终都在关注着病人,似乎总是在提醒我,在癌症的背后,是一个个与我们血肉相连、气息相通的个体。于是,当他诠释一个个与癌症相搏的故事,似乎也具有了超出个体的象征性的意义:这是一场一个物种与一种致命的古老疾病的恒久战争。在这场战争里,敌人拥有千万年物竞天择中演化出来的精妙而复杂的机制,体现的是自然界最核心、最原始、最顽强的生存需要与能力。
“每一个癌细胞,都是一个扭曲的、发展的、比我们本人更强大的、适应能力更高的敌手。抗癌治疗虽然不再是经验主义,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,但是你知道的越多,会发现后面还有更大的困难,明明知道依据现在的技术,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,不过你还是要往前走。”
他甚至提出了“学习癌症细胞一样的精神”,听的我目瞪口呆,但回过神来,却发现果然如是,叹为观止。他说,癌症是一个医学问题,一个统计学问题,一个社会学问题,一个心理学问题,也是一个人的问题。理解了癌症,或许就理解了人类的过去,现在,或许未来。“在达成理解的路上,很多生命,成了路边的野菊花,还有很多花儿,仍在等待。”
他坦言,有限成功不等于成功。“很多医生不愿意说治愈,因为不确定性,因为严谨,因为敬畏,因为他知道自己不知道。很多往前走的治疗方案,都是处于道德规范的边界。”
我从他的谈话里找到了一个词:求真务实。在治疗癌症的岁月里,他专心于他的思考,身体力行的实践,如今已有小成。二十多年前,他从南通到上海,就怀有这样的抱负。
我忽然想起他的一位南通同乡,一百多年前的清末实业家张謇,办大生纱厂、东华大学、海事大学,将上海作为创业和发展事业的窗口。他的一生证明:作为社会个体,既在原有社会结构下有所作为,同时又参与新的社会建构,思考和行动,既受制于历史,又在创造新的历史。这一点,与苦心孤诣与癌症对垒的他,又是何等相似。
将雨山云忽际天,
有时山忽上云颠。
晚来更被横风扰,
万点青苍尽化烟。
握手言别,我把这首张謇的诗,送给他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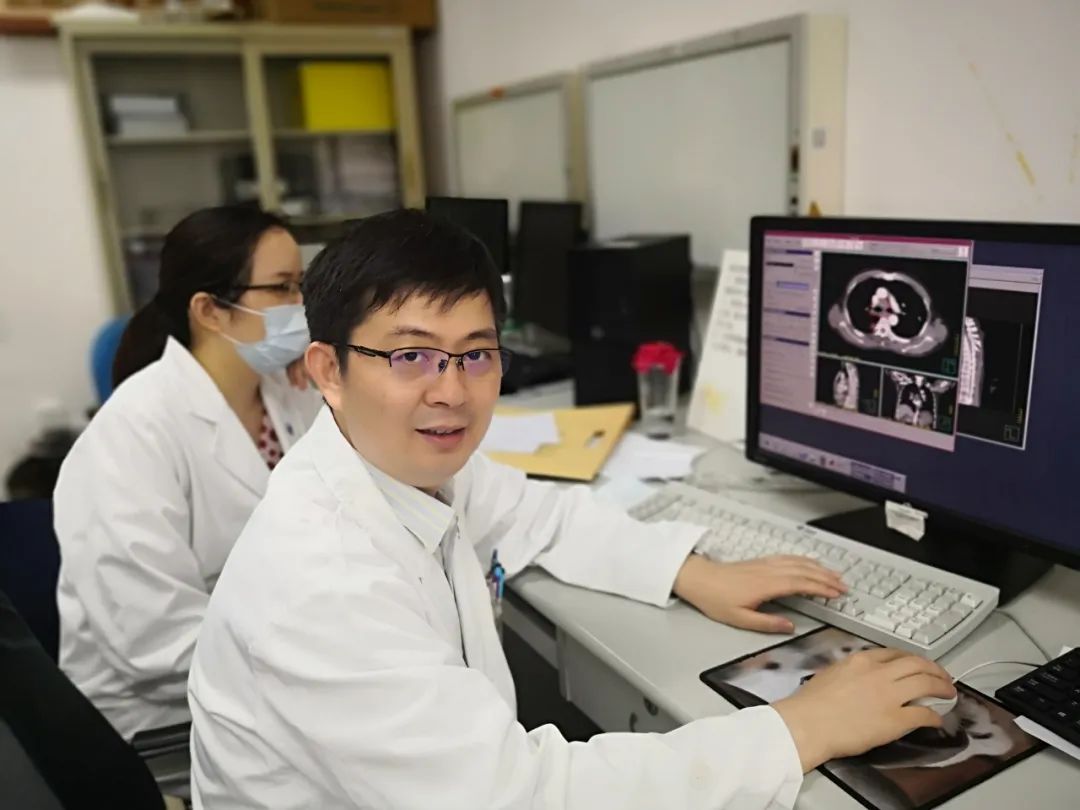
1
从医之路
1976年,朱正飞出生于江苏南通。
学医这个选择,很大程度上跟他的家庭有关。在朱正飞还不满十岁的时候,母亲患上了乳腺癌,在南通肿瘤医院住院治疗。
“母亲当年接受了乳腺癌的扩大根治手术,刀口几乎超过了整个胸壁的纵长,又经过了漫长的化疗。”当时肿瘤的治疗手段较少,相对简单粗暴,朱正飞至今都能清晰地回忆起母亲经历的痛苦。朱正飞十岁生日的时候,母亲在医院病床上,不能陪在身边。朱正飞说,那一天非常想念母亲,“老母与子别,呼天野草间”。揪心与牵挂,伴随他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十岁生日,不过,也正是那一天晚上,他坚定了未来的职业选择:学医,救人。
到了高考那一年,从第一志愿到第三志愿,朱正飞都填报了医学院校,最终,他考入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。
朱正飞说,从高中到大学,是身份与认知的转变。大学五年,他很“单纯”,除了读书,还是读书。本科毕业后,也许是冥冥中的安排,他一脚踏进母亲曾经在此住院的南通肿瘤医院,熟悉的建筑,熟悉的草木,让朱正飞感慨良久,他知道,多年前许下的愿望,终于有实现的机会与可能了。
轮转过后,朱正飞选择了放射治疗科作为专业方向。放疗是一门专业性强、融合度高的学科,定位要靠扎实掌握解剖标志,读片则要靠二维三维的影像基础和优秀的空间想象能力,还需要放射物理和放射生物的知识。在做小医生时,朱正飞到了晚上,一有空闲就在办公室捧着一个骷髅,观察头部的复杂结构,细细琢磨,在脑袋里拼成一个三维图像。
“这一枚骷髅,是从标本房里借出来的,跟着我两三年吧,我不知道它曾经的主人是谁,是怎样的人生,但我一定很感激他,在寂寞的夜晚,伴随我青灯黄卷的苦读。”
轮转四年,朱正飞对肿瘤学和放射治疗学有了初浅的认识,他意识到自己需要钻研什么、需要加强什么,也发现现有知识远远不够。于是,四年后,朱正飞考研进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,师从胸部肿瘤放疗专家傅小龙教授。巧的是,在2005年面临转博时,傅小龙教授也刚好评上了博导,朱正飞顺理成章成为了他的第一个博士,主攻肺癌。

2
生涯飞跃
“老师的性格里非常安静,他能够静下心想事情,想病人的治疗和学术发展,不受各种干扰和诱惑,这一点,我特别佩服。同时,他对病人非常负责,作为放疗科主任,他日常事务繁忙,但仍然对每张病床的病人情况熟稔于心。他从来不用翻病史,从一床到二十床,病人是什么状况、要注意些什么,了如指掌。”
傅小龙教授在全国放疗界有口皆碑,他对病人设身处地的考虑,给了朱正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“导师大我12,还在不断学习新的技术方法。他对事业有热忱的追求和独到的见解,很早就想着如何接轨国际上最新的治疗模式,并以惊人的践行力落到实处。而且,从不固执,愿意和研究生们讨论问题,对合理的补充,都能爽利地接受,难能可贵。”朱正飞说。
正因为此,老师身上的很多特性,后来慢慢也成了朱正飞的习惯——了解病人关心病人,把病人的利益作为首要考虑;不断进取和学习,力求自我完善。他一直记得老师的话:放疗科室除了放疗医生之外,还应该增加更多工科、生物等领域的跨学科人才。
“放射治疗专业性很强,需要各个学科的配合,需要先进的内科治疗手段以及生物物理技术支撑,需要更好地做到精准化诊疗——这些学科,在放疗的各个维度上应用价值都能得到体现。”朱正飞说,这就对放疗医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:首先要对现在的新技术和新方法有比较深入的了解,其次要站在医生的立场讲出自己的想法,并理解交叉学科的观念,擦出共同的火花,找出相应的交集,而这个交集往往就是能够发展和创新之处,也是朱正飞正在努力的方向。
朱正飞说,在傅小龙老师门下读研,也正是他职业成就感萌生的伊始,所谓风鹏正举,一飞冲天。
在朱正飞看来,成就感是由几部分组成的:第一,来自内心,这源于对自己的打分,感觉到比原来更加完善,这是“自我认同感”;第二,来自于他人的评价,包括导师对自己的认可,还包括放疗学界前辈、同僚、学会的认可;第三,令人满意的疗效。“也许这一点是最重要的。我希望对病人做出符合指南,又带有一些创新意义的治疗,在中国尤其重要的是,不进行过度治疗,病人还能获得长期生存,又有生活质量。”
2012-2014年,朱正飞作为访问学者,前往美国MD Anderson肿瘤中心。
国外访学分为两类,第一类是实验工作,进行基础研究,为晋升和课题申请提供一定的基础;第二类是临床工作,聚焦于国外医疗系统下病人的诊疗过程、效果和病人的感受。朱正飞的访学属于后者,他表示,的确感受到了与国内的差异:
“国外临床资料数据库很完善,比较研究非常方便。有了数据库的支撑,所以有更多的临床试验能够参与,有更多的研究手段和探索机会。这对国内的同行,是个重要的启发。”
3
有所为有所不为
从医20余年,说起病人,朱正飞如数家珍,对很多病例记忆犹新。
一个五年前的食管癌病人,发生了肩胛骨、腹膜与淋巴结的多发性转移,对各个部位都进行了积极的局部处理(放疗)。到如今,即便化疗已经停止五年,患者都没有发生复发转移。这也是朱正飞经常拿来教导进修医生的病例。
朱正飞表示,肿瘤治疗之前就应该对预后进行预判,是可治愈的(curable)、可能治愈的(potential curable)还是不可治愈的(incurable)?能用根治性治疗手段达到治愈的,就要尽量将这些手段前移,力求治愈,坚决不能用不可根治的手段。可治愈的早期肺癌,目前还是推荐手术治疗,不应该在没有临床入组的情况下,试验性地擅用一些方法,这是对病人的不负责。只有晚期的病人,才要尽量在其有生之年,保护生活质量和社会学行为,在此基础上适当延长患者的生命。所以,对肿瘤的生物学特性的把握,是非常重要的,这对治疗手段的选择,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基于这一点,朱正飞提到一个全身多发转移的女病人,经过培美+铂类的四疗程化疗,肿瘤退缩明显。按照传统理论,该病人需要进行培美维持治疗,但病人并不愿意。朱正飞和内科医生进行了讨论:这是一个生长缓慢的惰性肿瘤,直到2年多才出现孤立性病灶的进展,根据病人意愿,采用局部治疗可能就够了。
“没必要用靶向药物。靶向药物只是肿瘤抑制剂而不是杀灭剂,多数靶向治疗都会出现复发和耐药。而事实上,惰性肿瘤处在一个相对平衡状态,就不必选择激进的治疗方案。”朱正飞这样解释:这类肿瘤就像是会吃人的“狮子”,手头的治疗武器相当于一根筷子,用筷子杀死一头狮子,可能吗?当然不可能。但现在肿瘤处于相对缓慢静止的状态,就像是狮子睡着了;如果强行治疗,就是用筷子去捣狮子的眼睛,如果刺激了肿瘤,狮子就会“吃人”。朱正飞的选择是,密切观察狮子的状态,如果有醒来的预兆,就用“筷子”点一个“穴”,让肿瘤尽量处于休眠的状态——这就是密切把握肿瘤生物学特性的艺术。
朱正飞这样理解人和肿瘤的关系:和病毒细菌这类病原体不同,肿瘤起自人体本身,由正常细胞恶变而来,是人类自己的“孩子”——不过是个坏孩子,因此,治疗肿瘤相比于治疗体外的病原要难得多。同时,既然是自身长出来的,就会和人体达到相应的平衡,但这种平衡需要外力的帮助,譬如对肿瘤的杀伤和对人体免疫功能的调节。另外,在肿瘤诊治的过程中,人体的其他社会心理因素,也会对肿瘤产生影响,譬如情绪、性格、价值观,都可能改变自身的免疫力。
和肿瘤打了多年交道,作为放疗科医生,朱正飞说,肿瘤是复杂而狡猾的,需要的是不是单一局部治疗,而是基于全面考虑的综合治疗。
“说句戏言,人类需要具有肿瘤细胞的某种精神。”朱正飞说,“首先,它能批评和自我批评——肿瘤为什么会对药物耐药?因为肿瘤会改造自己,自我批评自我反省,能在夹缝里求生;其次,它会利用资源,比如周边的旁路、新生的血管和营养物质;第三,它非常具有合作精神,比如肿瘤细胞之间的crosstalk;最后,它还很善变,能够适应时代的潮流。”和肿瘤斗争这么多年,朱正飞认为,肿瘤的这些精神,在人类学、社会学方面也同样适用。
如今,科技进步、学科发展,肿瘤治疗的手段和方法有了更多突破,更多病人有了长期生存的可能。朱正飞说,医生就像战士,敌人是肿瘤,要扛住或杀灭它,仰赖各种各样的武器。关键的问题是,手头的武器是否适合病人。
他这样比喻道:“大炮很猛,去打蚊子行吗?手枪不错,去打一个军队可能吗?所以,对肿瘤生物学特性的认识,在选择武器的过程中非常重要。”